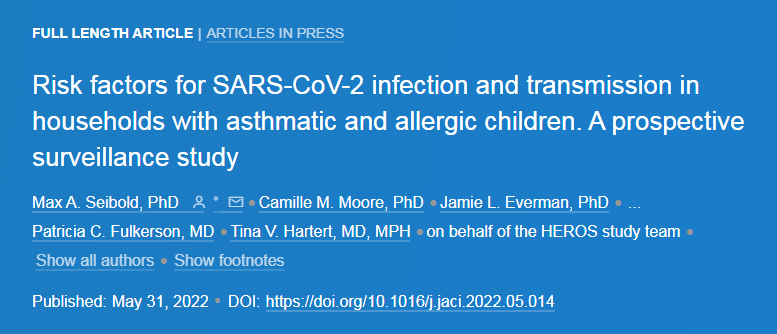远隔万里,身处异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种阖家团聚的欢乐气氛,令我深感欣慰。父母双全且无病无灾,这真好!兄弟姐妹手足情深、家家平安,这真好!虽不富裕却也没有衣食之忧,孩子们不必羡慕同学的新衣,这真好!读完老弟的信,我感叹一声:“庸人之乐,乃天下人之乐也!”我对于虽薄有文才,却极少雄心的老弟,倒生出些许的羡慕来。
18岁那年,我用网兜提着一个搪瓷的洗脸盆,背着大红大绿的背包出门远行。此后,和父母相聚、与兄弟姐妹相处的日子,就少而又少了。青春岁月时,很少想这样一个问题:我出门在外,父母肯定会刻骨铭心地想念我、牵挂我。可是,一过40岁,如同翻过了一座山一样,虽然我奋斗的雄心未减分毫,回望老家的目光,却是越发地沉郁、温润与热切了。
有时候我想,在我渐行渐远的人生行旅中,其实错失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人间快乐,比如,和儿时的朋友们去家乡的乡镇上“杀馆子”,以我可笑的一点财力,没有哪一家馆子是令我望而却步的——兄弟们呼啸而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该是何等的快活!再比如,带着众多的侄子侄女、男女外甥逛商场,享受一番“大伯”、“大舅”呼唤之声不绝于耳的“威风”,又该是何等的快活!再比如,根本不会打麻将或扑克的我,和众多的弟弟与妹夫们,来一场“窝里斗”,反正谁赢谁输,“肉都烂在锅里”,图的只是千金难买的全家乐气氛。
记得有一年回家探亲,一家人聚桌牌戏,老弟和二妹夫赢了我一点钱。老弟说:“你认输就算了,别把买飞机票的钱输光了。”我回答他说:“你放心,‘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听这话,老弟就“嘿嘿”地笑起来,和妹夫联手“围剿”我的劲头就更大。
求“庸人之乐”而不可得,这大概也算是将人生的目标定为“迎风远扬”的一种牺牲和代价吧?父母虽在而不能相守、兄妹虽多而鲜能相聚,这更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本质上的凡夫俗子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时,我内心深深祝福的,不仅是我的家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家人。能生活在一个吉祥的,而非暴戾的国家,受仁慈的,而非专横的政权统治,缴纳合理的,而非暴敛的赋税,拥有充分的,而不是部分的人权,享受有度的,而非滥用的民主,这就是天下的福份,这就是人间的乐园了。
我突然发现,“回家吃饭”这四个字中,竟然蕴涵着如此深厚的内容。有许多人,他们在官场中讨生活,多的是席间的敬酒与罚酒,无论“敬”与“罚”都不外乎“升”与“贬”;有许多人在商场讨生活,多的是席间的讨价与还价,无论“讨”与“还”,都不外乎“赚”与“赔”;还有许多人在海外讨生活,每天要面对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账单,生存的压力与精神的孤寂,是这些“无根之萍”的两大劲敌。
在自己的国家,回父母家吃饭,这看似简单不过的事情,对这些人却极为难得。去年夏天,回了老家荆门一趟。承蒙家乡朋友的抬举,我这个海外游子,受到了家乡的热情款待。大大小小的宴请,让我受之有愧。遗憾的是,在家乡半个月,原本指望能陪父母到菜场买菜,帮父母下厨,邀约兄弟姐妹全家聚会,这一心愿竟然泡了汤。
我不敢说“为名所累”这样的大话,因为,凭心而论,我仅限于家乡的这一丁点文名,纯然归因于家乡的高看与文友的谬赏,全然不可当真。故乡当真的,是那份给游子回家的感觉。可是,我回到荆门这个老家,却回不了父母那个陋室中的家。这却是我难以出口的隐衷啊!
春节前,打电话给母亲,问她准备了年货没有,顺便请教家乡特有的一种被称为“卷”的菜是如何做的。
其实,我大致知道其制作方法:将猪肉和鱼肉剁碎、放入葱花、豆粉、鸡蛋等,搅匀,搓成卷状,以蛋清抹在面上,入蒸笼蒸熟,切片装盘,即可上桌了。这道菜,类似于午餐肉,却比午餐肉鲜嫩可口多了。我以前在四川,后来在美国,都多次抽空试做过,无一成功。向母亲讨教后,如法炮制,味道、形状还是相差万里。
家乡独有的菜肴,或许只有家乡的肉、鱼与水,才能做出它的真滋味,这话,信不信,由你。
聊可欣慰的是,那次,在大弟家,承弟媳的美意,倒是让我吃上了两样稀罕东西。一样是“地皮”,老家小村里,村民们称为“地茧皮”,我觉得这个“茧”字多余,且有点不美,姑且将它略去。
家乡梅雨季节,阴雨连绵,长达两三月。乡间田埂上,常常可见这种黑色的菌类,一小片一小片捡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淘洗,端上桌,就是真资格的天然食品呢!如今我居住在旧金山,雨季从头一年的11月,延伸到次年的2月底,我家门前就是有“都市森林”之称、全球最大的人造公园——金门公园,草地上时常可以见到白嫩的蘑菇,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地皮”,否则,我一定要采点回家,让儿子开开眼界了。
那次吃到的另一样好东西,叫做“咋辣椒粉”。“咋”是家乡土话,标准汉语里没有这个词汇,但标准乡音里却少不了这样东西:黑黑的面粉,加上又红而黑的干辣椒,经过多次的翻炒,变得又焦又香,舀几匙盖在饭碗里,就可以香香地吃掉两大碗米饭。如果这种粉里,还加进了切得细碎,且泡得酸度绝佳的藕丁,我保准舍熊掌而就之,毫无悔意,只呼“快哉”!
在我的记忆中,几近赤贫的乡村生活,真正让我感到美丽、温馨与宁静的,其实是老百姓的诸种手艺,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好友、荆门籍诗人韩少君诗中所写的“使泡菜坛子充实”的那些民间技能。
那是生活的至高艺术。下次回老家,我要向母亲当面请教,如何制作“卷”、腊鸡、干鱼、酸菜,向父亲学习如何做豆饼、糍粑。母亲当然是灶间的好手,但是,与过世多年的奶奶相比,却是差了一截。我这样说,母亲肯定不会见怪,因为这是母亲亲口承认的。时光是如此的残酷:我渐入中年,父母已然呈现暮年老态了。
我终有留不住父母的一天,却至少可以凭藉着学自父母的这几样手艺,把各自成家立业的兄弟姐妹们聚拢在一起,重温那几十年的呵护、牵挂、责骂甚至殴打,一点点一滴滴,都是爱,只有爱。
无端想起小时候的一幕情景:我家隔壁,住着一户程姓长辈,官居大队支部书记,是全大队共8个小队、数千人口的最高领导。
那时候,农村没有电,到处黑咕隆咚,村民都睡得早,大概8点多钟,村里就很少有人走动了。每当我们上床,迷迷糊糊之际,总是会听到村子中心传来一阵声震四邻的呼唤:“建设,回家吃饭!”呼唤他的,不是他的奶奶,就是他担任接生员的母亲。一般要喊好一阵,才会听到这野孩子从远处不知谁家回应一声,接着就是一阵“蹬蹬”的脚步声;如果是他的父亲亲自站在街头喊他,通常是这样喊的:“建设,回家吃饭!再不回来,老子一砣子(拳头也)把你的脑袋砸到脖子里去!”乖乖地,不等第二声,那野孩子就跑回家了。
“建设”乃是乳名,是我的本家老弟,听说目前在家乡当个镇长之类的官,比他当了一辈子支书的老爸,可是大了好几级。虽是芝麻官,官场的应酬,却并不像芝麻那样小。我寄望我的这位老弟,也记得小时候母亲夜晚唤他的那一声高喊:“回家吃饭!”
家里的饭,大多是粗茶淡饭,比不得场面上那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但可以吃得舒坦,吃得放心,因为那是真正的“安生茶饭”。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