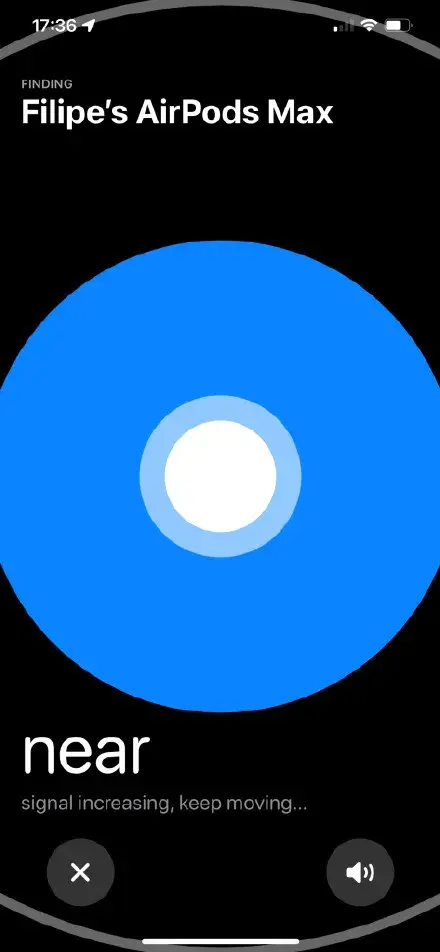广场中央巨大的火把已经熄灭,穿着节日盛装的彝族人也停止了打歌,庆祝火把节的人群却还不肯散去。狂欢者将松明粉抛洒进一个个小火堆,霎时间蹿起明亮、盛大的火焰,伴之以阵阵惊呼。
年轻的警察一边维持着秩序,一边向好奇的游客讲述火把节的传说。彝、白、纳西、拉祜等多个西南民族都庆祝火把节,节日的来源众说纷纭,在巍山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火烧松明楼”。
唐朝时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域有六个部落,称为六诏。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逻阁意欲兼并各诏,以祭祖为名,邀请其余五诏首领于松明楼聚会,趁众人酒醉之时纵火,五诏首领都死于火中。公元738年,六诏统一,南诏国开启了两百余年的统治。
巍山火把节 (黎瑾/图)
西边大寺:重访蒙舍诏的崛起之地
“诏”在彝语里是“王”的意思,蒙舍诏在六诏中地处最南,因此又称南诏。今天的巍山一带便是南诏的发祥地。
据《南诏野史》记载,蒙舍诏的建立者细奴逻原本居住在哀牢山,为了避难而迁居蒙舍川,躬耕于巍山,于649年建蒙舍诏。他率领族人励精图治,在龙于图山筑城,这是南诏政权最早的城池。细奴逻向唐朝进贡,派儿子往长安觐见,由此被唐朝授予巍州刺史。
龙于图山位于今日的巍山古城西北15公里处,从古城前往不过半小时车程。道路从青翠的田野边经过,随后与牛群同行,转过一条条盘山的弯道之后,两条土路出现在前方。我们开窗向路人询问,小伙子热情地指点:两条路都可通往山头,整片山头都是西边大寺。
传说火烧松明楼就发生在龙于图城,一千多年过去,城池早已深埋地下,唯有圈起整个山头的文物保护区界桩提醒我们,此刻已身处南诏的兴起之地。城址中挖掘出了寺庙、宫室等建筑遗址,出土有莲花瓦当、莲花纹方砖、柱础,以及大批雕刻精美的佛教石刻造像等文物。如今,在南诏第一座城池遗址的西南侧,布满了大小殿宇五十多座,组成了庞大的宗教建筑群,因位于巍山坝子的西边,被当地人称为“西边大寺”。
车开到高处停下,我沿着小路走进西边大寺,目之所及皆是庙观,建筑依山势高低错落,翻新的门墙与古旧的楼阁夹杂。西边大寺一直有当地乡民自筹资金修复与维护,因此旧瓦片之下常见颜色明丽的斗拱,老立柱旁也有新贴过瓷砖的祭台。
建筑密集,我们沿着小路与阶梯随意探索,从高处金碧辉煌的财神殿走到山腰处照壁雪白的孔子殿,再经过观音殿,阶梯向上通往祭祀细奴逻之妻的三公主殿……寺庙寂静,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拜访者。葱郁的大树掩映着古老斑驳的壁画,我轻轻推开一扇扇雕刻精美、虚掩着的木门,从褪色的牌匾下跨过磨损的门槛,望见几束阳光照亮观音、佛祖、玉皇、吕祖、太上老君、孔子等神佛先贤的塑像。如同漫步在一座立体迷宫,凡人小心翼翼地穿梭于各教神仙的殿堂。
山风摇动铃铛,我循声抬头,望见一龙一虎立在飞扬的檐角之上,阳光穿透浓密的枝叶洒落咆哮的老虎,长长的虎尾盘在立柱之上,当真是栩栩如生。再往下,一扇小门上书“云隐寺”三字,揭示出西边大寺原本的名字与漫长的历史。
西边大寺本名“云隐寺”。 (黎瑾/图)
据《蒙化志稿·祠庙志》记载,云隐寺最初由细奴逻建立,明代时进行了扩建。最初这里是佛教寺院,之后随着道教兴盛而建起道观,再与当地彝族的土主信仰混杂,外加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文化,逐渐形成了佛道巫三教合流的局面,而寺庙木门之上也清楚地写着“三教一礼”。
寺庙门上的“三教一礼” (黎瑾/图)
因山顶建有道观斗姥阁,云隐寺又被叫做天姥崖或天姥寺,徐霞客曾来此游览,写道:“蒙化有四寺……而天姥之名最著。”可我觉得还是云隐寺之名最为贴切,正如此刻的浮云聚散无常,古刹隐于山中。站在殿宇之间,我的目光向下越过重重叠叠的斗拱与檐角,俯瞰着山脚的坝子——白云轻柔地覆在连绵的山巅,这片稻田会不会就是细奴逻耕种过的田地?
从高处俯瞰依山而建的西边大寺与山脚的坝子。 (黎瑾/图)
巍宝山:走进南诏土主庙
巍山古城完好地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与风貌,主街贯穿南北,连接起两座巍峨的城楼,靠北的拱辰楼气势恢弘,靠南的星拱楼秀气古朴,老居民还在老街巷里过着寻常的市井生活,时不时能看见身着民族服饰的乡民来城里采买。
自细奴逻起,南诏便深受儒家文化的洗礼与熏陶,统治阶层学习和推行唐朝的礼乐制度,儒学从上至下地广泛传播。尽管是彝族自治县,巍山的传统文化底蕴之深足以令汉族地区自愧不如——古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用词文雅、考究的对联,我常常经过几家专门写字的店,拿着毛笔的老爷爷坐在小桌前认真地书写着城内红白事的告示。
巍山古城的老居民在老店门口临帖习字。 (黎瑾/图)
细奴逻去世后被奉为巡山土主。“土主”是彝族原始的祖先崇拜形式,将本民族或本家族的历史英雄人物供为最具权威的保护神。随着南诏的兴盛,南诏境内以乌蛮(彝族)、白蛮(白族)为主的各民族将两百多年间历经的13代诏主都奉为土主。总土主神为南诏始祖细奴逻,在古城以南的巍宝山建有南诏土主庙进行祭祀。
即便夏日的人流挤满了大理州各处景点,巍宝山依然保持着清幽。茂林修竹掩映着散布于山间的近20座道观,其中不乏清代留下的木构古建。进入山门不多远,我们就来到了南诏土主庙。庙宇初建于南诏第三代诏主盛逻皮时期,后因战乱毁坏。现在规模宏大的建筑是本世纪初维修扩建的,这是西南彝族地区规模最大的土主庙,每年都举办彝族祭祖节。
庙前的广场立有彝族的图腾柱,照壁上的浮雕讲述了彝族的历史与神话,庙宇的牌匾与对联都采用了汉字与彝文两种语言。跨进土主庙门,只见草木青翠、古树笔挺,祖灵殿显得安静肃穆。壁画的内容来自佛教进入南诏的传说:观音化为梵僧,传授第一代诏主细奴逻和第二代诏主逻盛治国之道,襄助南诏建国——但因巍宝山是道教名山,改为了老君点化细奴逻。
祖灵殿的壁画描绘了老君点化细奴逻的故事。 (黎瑾/图)
再往后,南诏彝王大殿矗立在高台之上,苍翠青山映衬着庄重宏伟的建筑。我们拾阶而上,走进殿内,大殿与两边侧殿塑有历代诏主的雕像,一一陈列他们的生平与功过。有趣的是,南诏王室采用父子连名制,13代诏主的名字犹如成语接龙,细奴逻—逻盛—盛逻皮—皮逻阁—阁罗凤……南诏国的兴衰就在一个个名字变换中上演。
南诏彝王大殿供奉了13任诏主,主殿有细奴逻的塑像。 (黎瑾/图)
细奴逻建蒙舍诏,皮逻阁在唐朝支持下统一六诏,阁罗凤叛唐、与吐蕃联合,异牟寻再归顺唐朝、被封为南诏王,劝龙晟统治时南诏王权开始衰落,世隆时期南诏与唐朝长期战争……最后一任诏主舜化贞死后,南诏灭亡。两百多年来,南诏与唐始终关系密切。
太和城:登上南诏古都遗址
皮逻阁无疑是南诏最重要的一任统治者。历史当然不像火烧松明楼的故事那样简单,吞并五诏是一次次攻伐的胜果,背后必不可少的是唐王朝对皮逻阁的支持。
在第四代诏主皮逻阁时期,南诏的势力已从巍山北上至苍洱地区。737年,皮逻阁通过又一次征战,占据了位于苍山的太和城。这里原本是河蛮(苍洱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部落)的城邑,本身已颇具规模。次年,皮逻阁统一六诏,唐朝封他为云南王,南诏正式立国。739年,皮逻阁将南诏的统治中心从巍山迁至太和城,这是南诏国第一座王都。
从巍山往北至大理下关,顺着洱海西岸继续北行至太和村,道路西侧的苍山佛顶峰麓便是太和城的所在。我站在山脚眺望,想象古代的城邑巍然屹立在缓坡之上,往西靠着险峻的苍山,往东朝向苍茫的洱海,山海自成屏蔽,南诏国以此为中心进一步壮大。
确实也只能靠想象了,时过境迁,地图上圈起属于太和城的范围如今覆盖着山林与耕地,几乎没有留下可供常人辨识的东西。沿着公路上至山腰,又一个路牌出现在道路左侧,指出沿阶梯登山可到达金刚城的遗址。这是太和城的内城,位于太和城的西端、地势最高的山顶处。
我顺着小径一路向上攀登,林木苍郁、山野幽静,蜂蝶在野花间飞舞,清脆的鸟鸣偶尔从深处传来。山路崎岖,疯长的野草几乎遮蔽了阶梯,也掩盖住了依山而立的一座座坟墓。接近山顶时,前方出现了一道荒草萋萋的土梁,标识牌告诉我这就是金刚城的城墙。
金刚城以夯土筑墙,或许我脚下踩着的土路就有来自城墙的遗留。小径还在向前延伸,我在近人高的草丛中勉力行走,又路过一段已经与山林融为一体的北城墙遗址后,终于抵达了最高处。鹤顶寺矗立在草木环绕中,寺门上写着“白王府殿”,还挂着“南诏避暑宫”的牌匾。
金刚城遗址最高处的鹤顶寺 (黎瑾/图)
金刚城亦是南诏避暑宫的所在。虽名为避暑,但严密的城墙和高踞山顶的位置,说明了这座行宫同时具备相当的军事防御作用。千年之后,山顶只余断壁残垣、蓬蒿丛生,直至清光绪年间,乡人募资在此重建白王府殿。到了上世纪末,府殿已毁,于是当地人再次筹资重建鹤顶寺。当我走进寺门时,庙宇正在进行又一次翻修,瓦砾遍地,几个工人挑着沉重的水泥从登山小径走来。
寺旁有一道西城墙的遗址,另一侧则是镜面铺就的观景平台。我极目远望,只见缥缈的白云从苍山升起,沉沉云雾缭绕着苍翠的森林,村庄铺满了山脚的坝子,一直延伸到水波浩渺的洱海。苍洱之间,风流云动,不知见证了多少王朝更迭、古国兴衰。
唐天宝九年(750年),南诏王阁罗凤因不满云南太守张虔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残暴对待与索取无度,起兵反唐。这次天宝战争以唐军战败、南诏转而依附吐蕃告终。
从金刚城下山,我顺着公路走到了太和城下的南诏德化碑。石碑饱经沧桑,但其上的字迹仍有大部分可辨。公元766年,阁罗凤郑重地将这座碑立于太和城城门处,碑文记载了南诏起兵的缘由和与唐修好的意愿。此时距离阁罗凤叛唐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南诏也趁安史之乱攻城略地、向外扩张。然而,碑文的字字句句都暗示着南诏夹在唐与吐蕃之间的复杂处境,以及为本国利益计不愿与唐长期为敌的生存策略。
779年,阁罗凤过世,异牟寻成为新一任南诏王。同年,南诏从太和城迁都于羊苴咩城(今天的大理古城西边)。吐蕃、南诏与中原王朝的战事继续,两军不敌唐朝,南诏也逐渐不堪吐蕃的税赋负担,双方矛盾激化。794年,南诏与唐在苍山会盟,重修旧好,并联合对吐蕃开战。南诏国在异牟寻统治期间迈入了鼎盛时期,疆域最大时包含了今天的云南全境、贵州西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越南北部、老挝北部和缅甸北部部分地区。
琢木郎村:探访南诏最后的秘境
清晨的雨水笼罩着沉默的山林,车沿着狭窄的道路往上攀升。一位服饰艳丽的彝族妇女站在路旁的房屋前喂鸡,红与绿的色调配上花团锦簇的刺绣在阴雨天中格外亮眼,瞬间唤醒了我因为漫长山路而晕沉沉的神经。
前一天下午,我坐在巍山古城的一家甜品店里随手翻阅桌上的书籍,老板见我手中的书页正好是一幅琢木郎村妇女的照片,不禁说道:“这么华丽的衣服只有琢木郎的人才会穿呢。”
“你们不这样打扮吗?”我知道老板也是彝族人。
“我们是普通彝族人,据说琢木郎的人是南诏的王室后裔,只有他们才能穿王室的服饰。”
公元9世纪末,在与唐长期战争之后,南诏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衰颓。902年,第十三代诏主舜化贞及王族八百余人被杀,南诏国灭亡。五年后,唐朝灭亡。两个多世纪以来,南诏的历史与唐朝的历史几乎相始终。
相传南诏灭国时,有部分王族被追杀至深山,眼见无路可逃,只能躲进一个山洞。蜘蛛迅速地在洞口织上了网,追兵至此见蛛网完好,便没有进洞搜查。王室后人从此在山中隐居,世代繁衍。
隐藏在群山深处的琢木郎村 (黎瑾/图)
琢木郎的确隐于群山深处,在新铺的公路穿越重峦叠嶂之前,山村几乎与现代社会隔绝,成为荒野中的一处秘境。避世而居也让琢木郎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彝族习俗,近年偶有摄影团队来此拍摄,彝女鲜艳多彩的服饰、特色浓郁的打歌、完整的婚礼仪式逐渐吸引了更多的游人。
雨水稍停,我们沿着湿滑的石板路在村子里游逛。当地显然有发展旅游的意愿,村中正大兴土木,许多房屋已翻修一新,穿着红衣绿裤的彝女正站在高高的房顶上垒砖、抹灰。即便是老屋,墙面也粉刷过,还精心绘制了壁画,以彝文与汉字对应,图文并茂地介绍琢木郎的图腾、服饰、姓氏、信仰、节庆等等。比如,琢木郎村民多姓毕,这是蒙氏王族为避难而改了姓,而在洞口织网的蜘蛛则是琢木郎最重要的图腾之一。
我们从一户户人家门口经过,无论是背着背篓的,还是在老屋里堆柴火的,或是在院子里择菜做饭的,妇女都穿着传统的彝族华服。色调以大红大绿为主,罩衣、背心、围裙、裤子全都绣满了山茶花、杜鹃花、蝴蝶、石榴等各种花样,仿佛群山的鲜花绿树都被她们揽入服饰之中。这样张扬的配色在彝族中也相当特别,或许真是因为传承了宫廷风格。一针一线都是琢木郎彝女亲手缝制,她们就带着寂静深山里最耀目的色彩劳作、休息,至今已逾千年。
琢木郎村村民正在堆柴火。 (黎瑾/图)
若是在节庆或婚礼时前来,还能看见彝女戴上高耸的头冠。当地人称之为“头囊”,顶端扎有大红绢花,后端垂着点缀有红穗的串珠,此外额头上还有两个宝塔状的帽花。这种装束和《南诏图传》里描绘的南诏王族束的椎髻颇为相似,也许可算是琢木郎为南诏王室后裔的证据。
898年,舜化贞授意臣属绘制《南诏图传》,作品分为“图”(画卷)和“传”(文字卷)两个部分,用类似连环画的形式讲述了南诏的历史和佛教在南诏的传播。《南诏图传》现藏于日本,我们只能从琢木郎的仿制壁画中一窥古国的风貌。
服饰艳丽的妇女走过介绍彝族服饰的壁画。 (黎瑾/图)
雨天的山村格外幽静,唯一的热闹是探出门头的一丛丛湿漉漉的三角梅,唯一的声音是村民赶着牛羊从房屋间穿过。
“你们好,来玩吗?”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奶奶看我们在琢磨壁画,笑眯眯地打了个招呼。
我们连忙点头:“今天火把节,你们在哪里过节?”
“在广场,晚上点火、打歌。”老奶奶指向村庄深处,热心地解释。可惜当地人口音浓重,我们只听了个大概。然后大家挥挥手告别,老奶奶回家准备庆祝彝族最盛大的节日,我们也告别南诏古国最后的遗留,朝着节庆活动繁多的巍山去了。
黎瑾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