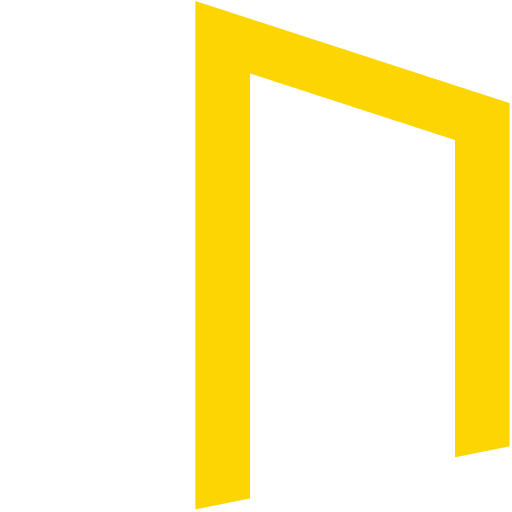早上六点的闹铃刚响,我就在黑蒙蒙的清晨醒来,迅速伸手将收音机闹钟关掉了。我是想在不吵醒妻子萨姆(Sam)的前提下悄悄溜下床。她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上班。我穿上前一晚放在床边的紧身裤,套上一件萨姆的毛衣。

我推开公寓楼的大门,看到一月的雨在黑暗中倾盆而下,卡车湿淋淋的轮子嗖地碾过第一大道。随着雨滴从伞面上弹落的节奏,我开始在脑海中反复默念:这都是为了孩子。这都是为了孩子。这都是为了孩子。
45分钟后我走进诊所,那时天还没亮。接待员打招呼时直呼我的名字:“你好,劳拉。请先坐一会儿。”
等待的时候,我拨弄着手腕上朋友送我的求子手镯。仅仅数小时之前,我和萨姆还睡在我去新奥尔良买的求子巫毒娃娃旁边。我甚至把一缕自己的头发别在娃娃的躯干上。有时我会盯着这些护身符想,给我一个孩子吧。
体外受精针(IVF)所有图片由作者提供
两年前,同为29岁的萨姆和我做了 卵子检查。令我震惊的是,我被诊断出不孕症,我的卵巢储备功能不足,如果不借助药物或生育治疗,我就没法通过 “正常” 的方式怀孕。这不仅意味着我难以受孕,而且即使成功怀孕了,流产的风险也很大。
虽然萨姆的 “卵子多得要溢出来”,但她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中包括子宫肌瘤。我们俩谁都不适合受孕,不过我们的医生建议,如果我真的想怀孕,就得尽快尝试。不久我们就挑好了我们认为合适的捐精者,买下他所有的六瓶精子。
接受生育治疗的患者需要每天监测身体状况 —— 通过血样分析和阴道超声波检查来判断卵泡的成熟情况 —— 因此诊所只会在正常办公时间前提供检查,那意味着还没天亮我就要在候诊室等很久。两个月前,在那个下着雨的冬日早晨,我在为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IUI(即宫内人工授精,就是将精子直接导入子宫促进受精的一种人工授精方式)做检测。我一直在吃药刺激卵巢,但医生明确表示,如果三次 IUI 之后我还没怀上,我们就需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第三次 IUI 在一月份失败之后,我计划给牛津医疗保险不孕不育项目的护士打电话讨论 IVF 疗法,如果我和妻子还想怀孕,这就会是我们的下一步。IUI 指的是将精子注入子宫,而 IVF(即体外受精)是指通过外科手术从身体取出成熟的卵子,在实验室用精子使其受精。接着把这种方式产生的胚胎移植到子宫,像正常情况一样怀孕,直到孩子生出来或者流产。
从最初的卵子检查直到第三次 IUI,检查、购买精子(最昂贵的一项支出)、精子储存和其他相关费用总共花了我们9772.04美元。我们的替补方案 IVF 很可能每次要花2万美元以上,还得加上每天去找医生验血、做超声波检查的费用。我用 IVF 怀孕的几率是35%到45%,IUI 则是8%到12%。
决定进行下一步之后,我们想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医保承担部分费用。可惜牛津医保对不孕不育的定义是 “一对男女一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对我和萨姆不适用。我们没有能够覆盖 IUI 或 IVF 的保险,但即使是其他的医疗保健机构也 没有把采取这些手段的同性配偶纳入保险范围内。
不像我们的朋友在停止避孕后就能怀上,对我们来说,“努力” 并不包括规律的性行为。我一直为不能与妻子生孩子感到遗憾,我想生一个跟萨姆一样有着绿色眼睛的孩子。相反,我必须躺在台子上,脚后跟箍在金属镫形支架里,通过 IUI 的方式让陌生人的精子注入我的子宫,或是身体被麻醉后,通过 IVF 手术来产生一个 “试管婴儿”。
二月中旬,我去新医生的诊所咨询我们的替补方案 IVF。第二天,萨姆和我又得回来赴另一个约 —— 按规定必须参加的 IVF 课程。等待课程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桌子后面的姑娘说:“今早你要缴一笔钱。”
头一天我们已经用两张信用卡平摊了11250美元的费用。
“我们不是已经预先付清了吗?”
她没答话,只是拿来一个彩印的包装盒,把 “ 冷冻胚胎移植(FET)” 几个黑体字圈出来。意思是说,我的卵子通过 IVF 受精时,实验室还会把同时形成的其他胚胎冷冻起来,用于下一次移植。我看到旁边的数字,眼中涌出了泪水:4260美元。我局促地让她等我一会儿。我们已经花了2万多美元,而 IVF 并不能保证我会怀孕。再说了,我们的课也没开始,我们自己还在摸索要怎么做。嘴上说你愿意为孩子花多少钱一点不难,等到真的需要掏钱的时候可就犯愁了。
一开始的惊讶过去后,我们冷静下来,勉强交上了额外的4260美元。
IVF 课堂上,我和萨姆与一群不知所措的男男女女坐在医院的会议室中,观看一个90年代的视频来学习 IVF 治疗的基础知识。每个女人所需的 IVF 疗程时间不同,但都是从月经第一天开始,此后你得每晚注射各种激素类药物,从而刺激卵巢产生卵子。一些药物需要在皮下注射 —— 打进我们的腹部或大腿处 —— 其他的要在臀部的上象限进行肌肉注射。一位疲惫不堪的丈夫问道:“要是戳到骨头了怎么办?” 护士给我们分发了针头和假人用来练习。
开始注射药物后,你得继续每天到医生那儿验血、做超声波检查,他们才能知道你的身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第二步 —— 促进卵子释放的 “触发针”。实行第二步的两天后,通过手术将卵子取出(如果有能够继续发育的卵子的话),在实验室中受精,然后培养出的胚胎 —— 即 “试管婴儿” —— 被移植回你的子宫。在那之后,要连续两周注射黄体酮增加怀孕的几率 —— 直到你要么来月经,要么就是成功怀上了。
我以为我们会有时间来消化这笔费用,弄清楚我通过 IVF 到底要把什么东西放进身体,结果我的月经提前了好几周,在上课的同一天开始了。我掏出钱包,拿回家一本小册子,上面用寥寥数语告诉我当晚要如何开始注射。
数小时后,我和萨姆把一个橱柜清空, 在里面装满了好多袋不同型号的注射针,一个红色的医疗锐器盒,纱布和酒精片,以及药瓶。我的前几针排卵针要用相对较小的针头,但萨姆在打头两针的时候扎了我整整四次。
她凑近我,用针头对准距离肚脐大概一英寸的地方,一旦感觉到针刺穿了我的皮肤,她就会吓得马上拔出来。我一点也不性感地背靠流理台站着,掐住肚子上的肥肉。我要求她:“你他妈冷静点,别磨蹭了。” 她扑向我。从那开始,我们每天晚上一人负责打一半的针。我会自己先打一针,让她打接下来的两针。药物副作用包括:肿胀、头痛、嗜睡、情绪波动、盗汗。(没错,我们的性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对于一对想生孩子的配偶来说实在是拙劣的讽刺。)
我们太紧张害怕把注射搞砸,浪费我们在这些必须的 IVF 药物上花费的巨款,这样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甚至也有可能我们一步都没有行差踏错,可仍旧怀不上。即使通过这更为昂贵的第二种疗法,我真的怀孕了,仍有可能会流产。我们还没想好愿意尝试多少次 IVF。我的妻子或许会自愿经受跟我一样的流程,但要想象当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万美元把我的身体注满了化学药品之后还要去尝试第三种疗法,这可真是让人难受。在繁琐的医疗程序中努力保持情绪稳定已经够难了,身体里流淌的激素更是雪上加霜。
从经期第一天开始每晚注射激素之后过了大约一周半,我的医生告诉我该打 “触发针” 来刺激卵子释放了。针头很大,我们俩都颇感忧虑。我说:“好,我们开始吧。” 我趴在流理台上,屁股朝向我的妻子。她将护士划了圈的那块地方消好毒,把针刺进去。我突然感觉一阵恶心,冲到厕所里。我跪在地上,对着马桶吐了个天昏地暗。我抱住马桶喘口气的时候,心想,这都是为了孩子。这都是为了孩子。这都是为了孩子。
劳拉·莉·艾比(Laura Leigh Abby)2016年1月通过 “亚马逊 Kindle Single” 发表了短篇电子书《匆忙》(The Rush),她的第一本实体书《两个新娘》(2Brides2Be)将由阿彻(Archer)出版社于2016年秋出版。你可以访问 她的网站。
相关文章